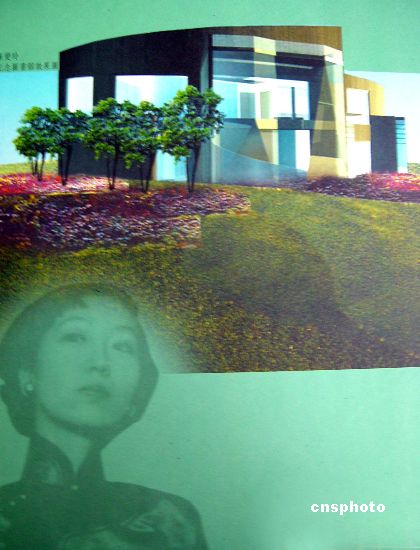
2002年资料图:倍受海峡两岸媒体普遍关注的“张爱玲纪念图书馆”工程,自2002年4月4日在位于上海市打浦桥地区的“东泰花苑”高级住宅小区内正式破土动工以来,目前进入桩基础工程施工阶段。这是台湾建筑设计师登琨艳先生来祖国大陆12年之后推出的第一件建筑设计作品,也是上海第一个以文化名人冠以名称,凸现其文化功能的住宅小区“会所”。 中新社发 李江松 摄
13年前的9月8日,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罗切斯特街道一所公寓的206号房间中离开了人世。她的遗体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一张相当精美的地毯上,一星期后才被人发现。桌上,有一叠铺开的稿子和一支打开的笔。
崇尚“出名要趁早”的张爱玲,1952年离开上海后在内地销声匿迹多年,直到改革开放后,开始在大陆“红得发紫”,并持续30年不减。
文学研究者、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内地,使得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(包括钱钟书、沈从文、林语堂、路翎等一批作家),像“出土文物”一样浮出历史地表。由此,才便有了《收获》刊出的《倾城之恋》以及文学界的相关评论。其后,张爱玲迅速走红,形成内地的第一次 “张爱玲热”。一批被尘封已久的作家,如钱钟书、沈从文等人,也因为夏志清的推崇而同期走红。
夏志清用42页论张爱玲
“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。”《倾城之恋》如此写道,而沦陷的上海,是张爱玲的成名地。
张爱玲,原名张瑛,笔名梁京,祖父张佩纶是清朝御吏,祖母是李鸿章之女。23岁时,张爱玲以小说《沉香屑——第一炉香》一炮走红,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耀眼明星。
对张爱玲研究产生推动的,是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。1961年,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出版英文著作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张爱玲首次进入中国文学史。
1979年,这部书的中文版在香港出版,并于 80年代初引起了内地学者的注意。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,内地与香港的交流逐渐增多,许多学者从香港带回了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。由此,张爱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。
作家止庵说,自己从一篇文章中看到,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用了26页论鲁迅,却花了42页论张爱玲,就很关注张爱玲, 1991年到香港,自己专门去买了夏志清的这本书。“夏志清在这本书里面推出了四个人,沈从文、张爱玲、钱钟书和师陀,前三个人因此名声鹊起并在海外引发研究热潮,台港一些著名作家如李昂、白先勇等人都对张爱玲推崇备至,这股风潮回过头来影响内地。”
写过《张爱玲传》的于青回忆,自己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,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。“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,思想解放之时,我们这批‘老学生’如饥似渴地找书读,越是开禁的,或未曾闻识过的,就越是有兴致。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‘库本’中找到张爱玲的《传奇》,当然还有钱钟书、沈从文、废名、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,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‘文学史观’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‘冲击’。不久,大概是1979年,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定: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。”
《收获》让张爱玲浮出水面
真正促成张爱玲进入内地文学评论界和作家关注的还是《读书》和《收获》。
1984年,《读书》和《收获》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《遥寄张爱玲》,又同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《倾城之恋》。自此,张爱玲作品进入大众视野。
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回忆说,柯灵《遥寄张爱玲》在写完以后,被当时《收获》杂志的负责人肖岱看到了,当时,这篇文章已经被《读书》约走了,肖岱认为柯灵的文章写得很好,考虑到《读书》和《收获》的读者对象不同,加上当时《收获》有一个介绍作家的作品专栏,每期推出一个,在刊登一篇作品的同时,也刊登一篇有关作家创作的评论。就这样,柯灵的《遥寄张爱玲》和《倾城之恋》一起刊登在《收获》杂志上。
程永新记得,“我们发表张爱玲作品,还是有一点点顾虑的。但是,她的小说确实很好,估计发出来即使有一些争议,问题也不大。”
《遥寄张爱玲》发表后,看过文章的张爱玲的姑妈和姑夫一起找到柯灵,感谢他为张爱玲说了公道话。
而作家阿城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:“一九八四年底,我在《收获》杂志见到《倾城之恋》,读完纳闷了好几天,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,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。”
作家苏童将张爱玲的一部作品选入“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”,称张的作品是“标准中国造的东西,比诗歌随意,比白话严谨,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”。苏童说,“我读张爱玲的作品,就像听我喜欢的音乐一样,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古典音乐,也不是交响乐,而是民谣流派,可以不断流传下去的。”
作家叶兆言甚至认为,张爱玲的作品让寝室的夜晚不再孤独。“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们一样,或是觉得张爱玲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。”
贾平凹把张爱玲称作“会说是非的女狐子”,看了她的散文,叫好不迭,又去找她的小说,在香港访问期间单挑张爱玲的书买。“当看到《倾城之恋》、《金锁记》、《沉香屑》那一系列,中她的毒已深。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,但偏要读。”贾平凹坦诚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迷恋。
在研究领域,根据学者艾晓明的回忆,新时期最早重新评价张爱玲的学者是北大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赵园,她写了《开向沪港“洋场社会”的窗口——读张爱玲小说集》,这篇文章比《遥寄张爱玲》还要早两年,后来收入她的论文集《论小说十家》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内地文学评论界内部对于张爱玲的评价也开始发生变化。 1985年,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等人出版了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,这是首次将张爱玲写入内地的文学史。在这本影响极大,被全国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使用的文学史著作中,吴福辉负责撰写了张爱玲的部分。在论及“孤岛”与沦陷区文学时,本书用了大约800多字来写张爱玲,指出张有“古典小说的根底”,又有“市井小说色彩”,展现了“洋化”环境中仍存留的“封建心灵”和人们百孔千疮的“精神创伤”。尽管有人后来认为本书评论张爱玲“笔墨相当经济” ,但是无数的大学生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,按照陈子善的说法,在高校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中,研究张爱玲的一直名列前茅。